发表时间:2026-01-31
浏览次数:73
>为躲避末日危机我独自缩进地下堡垒苟活十年。
>每天靠打游戏混吃等死,偶尔看看地上幸存者挣扎的监控录像下饭。
>直到有天在公共频道刷到条消息:
>“那个缩头乌龟,知道你父母怎么死的吗?”
>“他们跪在我基地门口求一口药救你高烧的命。”
>“我让他们学狗叫才给退烧针。”
>“你猜怎么着?他们真叫了。”
酸雨永无止境地敲打着合金舱盖,细密沉闷,像谁在不耐烦地用手指反复叩击棺材板。陈沉窝在浸满汗渍和人油味的电竞椅里,屏幕上是《荒野大镖客2》风雪连天的雪山,他操纵着约翰·马斯顿漫无目的地游荡,枪口对准一头虚拟麋鹿,扣动扳机。砰。麋鹿应声倒地。旁边分屏,十几个监控画面分割着地表废墟的不同角度,断壁残垣浸泡在铅灰色的雨幕中,偶尔有瘦骨嶙峋、动作僵硬的影子蹒跚而过,像贴在玻璃缸壁上的腐烂水草。
地下十层,“龟壳”。空气循环系统送出带着铁锈和过滤器过期酸味的恒温风。角落堆积如山的压缩饼干箱、维生素瓶和纯净水桶构成他世界的边界。十年。足够一个婴儿长成少年,足够文明彻底烂掉根须,也足够把一个曾经还会因为日出而心跳加速的人,磨成一摊只为维持基础代谢而存在的活肉。
他摘下滑腻的VR头盔,揉了揉发涩的眼睛,伸手从脚边的纸箱里摸出一袋酱牛肉味营养膏,挤牙膏一样嗦了一口。味道像锯末混合了过量的味精。视线习惯性地扫过监控分屏,没什么新鲜玩意儿。东三区摄像头下,两只“行者”正趴在一具看不出原形的尸体上啃食,动作机械而专注。他面无表情地切走了那个画面,点开西七区,那里曾是个小型人类聚居点,现在只剩几顶破烂帐篷在风雨中飘摇,空无一人。挺好,清静。
公共通讯频道大部分时间死寂,偶尔会有些意义不明的电流杂音,或者某个频段突然爆发出短暂而凄厉的惨叫、咒骂,然后迅速归于沉寂。人类的火苗,散落各处,正在一盏接一盏地熄灭。他早已习惯了这种背景噪音,甚至有点依赖,这能证明他不是宇宙中最后一个会喘气的。
当那个陌生的、没有任何标识归属的信号源,强行插入公共频道,并转化成冰冷平稳的合成电子音时,陈沉嗦营养膏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“呼叫‘龟壳’里的那位。ID:Chen-Chen-0731。”
1。”
陈沉的脊背下意识挺直了些。他的匿名ID,十年前设置后就没改过,知道的人……应该都死了。
电子音没有停顿,继续以那种毫无波澜,却字字诛心的语调播放:
“知道你父母是怎么死的吗?”
营养膏袋子从他指间滑落,掉在铺着杂乱线材的地板上,发出一声轻响。
“不是死于最初的混乱,也不是死于饥荒或感染。”
。”
陈沉感觉“龟壳”的氧气瞬间被抽空了,胸口闷得发慌。
“他们在灾变第三年的冬天,跪在我基地外围的隔离门前。那时候,你应该刚满二十岁吧?正躲在不知道哪个耗子洞里发着该死的高烧,奄奄一息。”
声音顿了顿,仿佛在欣赏他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的惊愕与逐渐凝聚的痛苦。
“他们手里举着一个破牌子,上面写着求救信息,还有你的名字和陈家老宅地址。他们相信那地方能联系上你,或者说,那是他们唯一知道的、可能找到你的线索。他们求我,赏一支退烧针,或者一点点抗生素。”
陈沉的拳头攥紧了,指甲深深陷进掌心,骨节泛白。监控屏幕上,废弃都市的远景在雨水中模糊变形。
“我看他们可怜。主要是无聊。”电子音里似乎渗入一丝极其微弱的、非人的笑意,“我说,学几声狗叫来听听。叫得让我满意了,说不定就给了。”
意昂2官网“你猜怎么着?”
陈沉的呼吸彻底停滞,血液冲上头顶,耳朵里嗡嗡作响。
“他们真叫了。”
“趴在地上,像两条真正的老狗,对着铁门,一边磕头一边头一边吠叫。呜汪…呜汪汪…真是……感人至深。”
合成音模仿了两声拙劣的狗叫,那声音比纯粹的纯粹的辱骂更令人毛骨悚然。
“后来呢?”陈沉的喉咙里挤出三个字,嘶哑得不像他自己的声音。尽管频道是单向广播。
“后来?”电子音轻飘飘地反问,“我让人从瞭望塔上,扔下去半瓶兑了水的过期生理盐水。就扔在他们脚边的泥地里。”
“他们千恩万谢,像捡到宝贝一样扑过去……”
“……然后呢?”陈沉的牙齿开始不受控制地打颤。
“然后?”电子音的尾调微微扬起,带着一丝残忍的玩味,“味,“我看着他们为了抢那点脏水,互相推搡,被闻声而来的而来的几只行者堵在了墙角。过程不太好看,我就不详细描述了。你没等到他们的药,对吧?”
通话戛然而止。
公共频道里只剩下沙沙的电流白噪声,比之前的死寂更令人窒息。
陈沉僵在原地。
时间失去了流速。几秒钟,也可能是几个世纪。他猛地从椅子里弹起来,动作幅度大到带倒了身后的椅子,哐当一声砸在地板上。他踉跄扑到主控台前,双手因为剧烈的颤抖几乎无法准确操作。他疯狂切换着监控画面的存档记录,根据对方话语里零星的线索——“灾变第三年冬”、“小型基地”、“隔离门”、“瞭望塔”——检索、排查。
手指重重敲击键盘击键盘,发出噼啪的脆响。汗水顺着额角流进眼睛,又涩又痛。
终于,画面定格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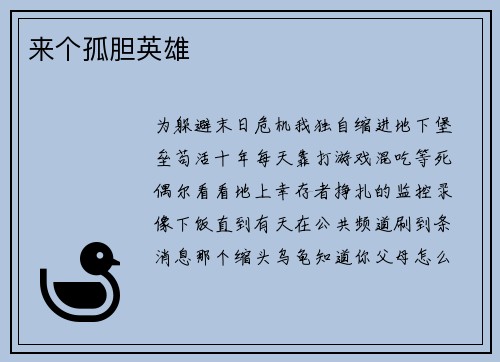
N-11区,旧世一座郊区工厂改造的避难所外围。监控日期:灾变3年,12月17日。下午,天色阴沉。
画质粗糙,布满雪花点。但他认得出来,那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!母亲!比他记忆中风华正茂的样子苍老了二十岁不止,穿着褴褛的、看不清颜色的棉服,蜷缩在冰冷的金属大门外。母亲不停地对着门上的摄像头磕头作揖,父亲则奋力举着一块硬纸板,上面模糊的字迹,隐约能看到他的名字和那个他以为无人知晓的老宅邮箱地址!
镜头视角来自高处,显然是对方的瞭望塔。他看到几个模糊的人影出现在围墙上,墙上,指指点点。然后,一个小小的瓶子被抛了下来,落在泥水里。他的父母愣了一下,随即几乎是手脚并用地爬过去……
就在这时,画面边缘,几个步履蹒跚、姿态、姿态扭曲的黑影出现了,缓缓逼近。
陈沉的心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,捏碎。
他看见父亲率先发现了危险,惊恐地把母亲往身后拉,想去捡那瓶水,又想拉着母亲跑,仓皇失措。母亲却挣脱了他,还想回头去够那近在咫尺的希望……
下一个瞬间,黑影淹没了那两个渺小、绝望的身形。
监控视频还在无声地播放着那片血腥的混乱,啃噬,撕扯。
陈沉死死盯着屏幕,眼球充血凸起,血丝密布。
十年。整整十年。他以为自己早已麻木,心如死井。他把自己变成一只缩头乌龟,藏在世界上最坚硬的壳里,用游戏、用麻木、用对他人苦难的冷眼旁观来麻醉自己,告诉自己活着就行,活下去就好。
可这一刻,那厚重的、用虚无和逃避浇筑的水泥外壳,在那段冰冷残酷的叙述和眼前这无声却震耳欲聋的画面面前,轰然崩塌!碎成了齑粉!
父母跪地的身影,学狗的哀鸣,为半瓶脏水相互争夺的狼狈,最后被行尸淹没的惨状……这些画面不受控制地在脑中交织、循环、放大!
“呃……”一声压抑到极致的呜咽从他喉咙深处溢出。
紧接着——
“啊!!!!!!!”
他猛地仰头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嚎叫,一拳狠狠砸在强化金属制成的控制台上!咚!沉闷的巨响。手背瞬间皮瞬间皮开肉绽,鲜血淋漓。
但他感觉不到痛。
只有滚烫的、足以焚毁一切的怒火,裹挟着滔天的悔恨、耻辱和自我厌弃,像岩浆一样从他的五脏六腑喷涌出来,灼烧着他的四肢百骸!
他剧烈地喘息着,胸膛起伏得像破败的风箱。通红的眼睛抬起,看向挂在墙壁上的装备架。那把陪伴他度过最初艰难时日,沾满污垢和干涸血痂的工兵铲,在应急灯幽绿的光线下,反射着冰冷的微光。
他一步步走过去,脚步沉重而虚浮。伸出手,紧紧握住铲柄,冰凉的触感顺着手臂蔓延,却丝毫无法浇灭心头的烈焰。
墙角的阴影里,传来他嘶哑、破碎,却带着某种十年未曾有过的、斩钉截铁的声音:
“我去你妈的……缩头乌龟……”
最后一个音节落下时,工兵铲被他从支架上猛地取下,沉重的金属铲头划破沉闷的空气,发出低啸。